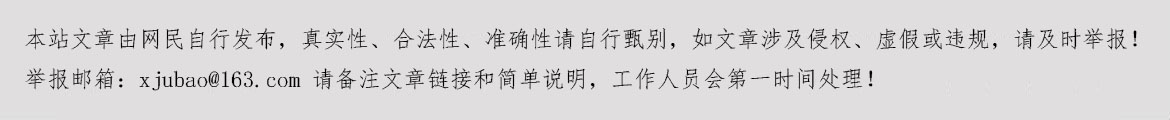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livings)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本文为“住在人间”连载第20期。
今年春节,我回济南陪母亲过年,又因为她患抑郁症开始药物治疗,便陪伴至今。算起来,这是我离家二十载后,在故乡待的时间最长的假期。以前都来去匆匆,只看到城市日新月异,却没有去多想那些在变化里消失不见的人与物——当然,也不愿多想。
直到这个充斥着疫情和困境的四月即将过去,春意微醺的深夜,独坐窗前,听到楼下河畔传来的蛙声,我才又想起那条街,一条消失了的街,还有那条街上消失了的人。
1
北光明街,它曾位于济南城北,属于天桥区北坦(坛tán)片区,走路十几分钟就到大明湖。北坦面积不大,但小街小巷错综复杂,拆迁前几年,片区内大多仍是鳞次栉比的平房,平房红砖外墙上满是灰色的水泥补丁。路边站着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连接着各家牵出的电线,杂乱密集得令人恐惧。
我小时家就在北光明街上,一座典型的济南老四合院,坐北朝南的大门口有青石铺成的三级台阶。进门穿过阴暗的门洞,是个长宽各五米的小院,院子地面比街道高出近一米,西、南、北各有三栋独立的屋子。北屋是正房,面积最大,被隔成内外两间;南屋临街,三十多平米;西屋方方正正,约十几平方;东边原本是院墙,后来搭了个简易的小厨房,小到在里面转个身都很难。
房子里是芦苇秆混着粘土的屋顶,外边房顶是瓦片,两者之间的夹层是土鳖虫和其他生物的乐土,我就曾被从屋顶上掉下来的土鳖砸到过。有时,躺在床上,会听到头顶窸窸窣窣有东西爬过的声音,零星的尘土随之落下。爸妈后来搭了一层薄薄的塑料天花板,算是解决了天降土鳖的危险,但虫子爬行和泥土掉落的声音从没停过。
我妈说,每家的屋顶上都住着一位大仙,大部分是蛇,也可能是黄鼠狼,甚至是老鼠,“大仙儿是一家的守护神,土鳖落在头上可能就是大仙儿逗你玩儿”。多年以后,我家房子拆迁,我妈信誓旦旦地说,她看到过一条大青蛇从废墟里爬走不见了。
自我记事儿起,我妈就神道儿(迷信)得很,什么用手指彩虹要烂手指头,正月里不能理发、不能穿浅色衣服,总有一堆说法。
有次,夏日黄昏,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她老家,有个女孩父母早亡,跟舅舅一家住,舅妈对她很苛刻。有次,舅妈带她出去办事,发现她跟一个小伙子眉来眼去,回家后就对她又打又骂,女孩一时想不开上吊了,舅妈就给她草草下了葬。后来,舅妈在院子里乘凉,偶然间扭头看了眼正房,结果看到屋里悬着个人,硕大的脸上没有五官,白花花一片,当场就吓死了。
我妈讲这段的时候,我正好对着黑黢黢的北屋,吓得立即就背过身去,头都不敢回,那种恐惧感尾随了我许久。
我妈什么神都信。厂里同事拉她去了趟教堂,她就带回来一本《圣经》,开始天天祷告、拜上帝。那本《圣经》摆在床头,被我从小当成儿童文学读得滚瓜烂熟,她却还没翻上几页。拜上帝也不影响我妈遇仙求仙、见佛拜佛,她秉持“只要给我办事儿就行”的实用主义,对漫天神佛都敬畏。
这或许不是偶然现象,济南历城区的华山华阳宫里面就供奉着耶稣、三清、孔孟、妈祖、黄帝以及那些鲜有人知的各路神灵,每家待遇都差不多,享有一个单独的小庙和祭坛。跟古罗马气势恢宏的万神殿不同,这个穷乡僻壤完全没有迎接万神来朝的野心,就是想着摆个摊儿让大家少走几步路,给人以心安,给自己多添几个香火钱。
后来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苏州的记载,说元代的苏州人家里供奉不同的神像,大部分人信仰不止一种宗教,看来这是大江南北从古到今的共同特点,也更深刻理解了“白猫黑猫”理论中所蕴藏的民间智慧。
从幼儿园到小学上学期间,我只有寒暑假才会住到四合院里,其余时间都跟着奶奶住在城南省委附近的机关大院——毕竟学校就在大院对面。那时我天天跟奶奶挤在一张床上睡,随着我块头越来越大,老人也休息不好了。我当时最向往的就是有个自己的房间,晚上可以随意翻身、蹬腿而不被骂。
这个愿望终于在我小学毕业时实现了——1990年上初中后,我开始长期跟爸妈住在北光明街上了。我搬回去的时候,家里刚通自来水(之前都要到双井街的公共水龙头挑水)。水池子搭在小厨房的门口,上面是葡萄架。由于管道架在了室外,冬天我家的自来水管经常会冻住,需要在水池子下面生火把冰化开。
平房烧炉子取暖用的是蜂窝煤,每年家里都要买很多,堆在西屋和北屋之间的小过道旁,上面用油毡纸搭了个棚子防雨。晚上封炉子早上起来换煤是冬天的日常,有时候炉子灭了还要重新生火,搞得屋里乌烟瘴气。
2
爸妈没有更早让我在自己家住,还有另外的原因。虽然这个四合院是姥爷留下来的房产,但曾经充公被重新分配。1980年,济南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解决公占私房问题的相关政策,只是,小院里其他住户以没分到其他住房为由拒绝搬走。就这样,又拖了五六年。
我爸妈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进行过一场场争夺战。
他们结婚以后住在南屋,有家人三世同堂住在北屋,西屋是个单身汉。由于我爸妈坚持要收回自己的房子,自然就跟其他住客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北屋的一大家子人。平时口角磕碰是家常便饭,大打出手也不是没有过。据说有次双方动了肝火,我爸还叫了七八个朋友到家里来“吓唬吓唬”一下对方。那次纠纷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有个姓高的叔叔是我爸同事,也在被“邀请”助阵之列,他临时有事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赶到四合院以后发现家里没人。从邻居那里打听到事情经过,他立刻赶去派出所,进门就开始大声嚷嚷:“还有俺嘞,俺和他们都是一伙儿嘀!”
我爸对这件事津津乐道,说那时候的人讲义气。我对高叔叔的印象也很深,因为他骨骼清奇(个儿矮),人有异象(丑得惊人),三角小眼黑麻子脸,大嘴恨不得咧到耳朵根儿,黄黄的龅牙参差交错,鼻毛从鼻孔里探出老长。他常常抱怨说先天营养不足,个儿没长高,后天要补上。他喜欢表现自己好汉的豪爽,我亲眼见过他用刀割生肉吃。他在厂里养着几只羊喝鲜羊奶,有时候,他干脆直接把羊摁住用嘴嘬奶喝。
我爸说高叔叔有次在厂里跟保卫处的人打架,对方高大魁梧练过摔跤,一拳就能把他打几个跟头。他挨不住了抱头蹲地,对手看这意思以为打完了,刚一愣神儿就被他猛地扑上来抱住脖子,一口咬掉了整只耳朵。众人大惊,连忙把他摁住,送伤者去医院。有人说咬掉的耳朵要一起带上,说不定还能接回去,结果他含在嘴里拒绝吐出来。大家费了半天工夫才让他吐出来,他又趁大家松懈时,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力踩住,还在地上碾了几脚。后来到了医院,医生看到那块从烟盒里拿出来还粘着烟丝的烂肉的时候,直接就让丢垃圾了。
工厂后来被兼并,我爸进入了新企业工作,高叔叔则和其他大部分人下岗自谋职业。他下岗以后在人民商场推着三轮车卖过磁带,城管、派出所的人都不愿惹他。后来,听我爸说他肝儿上检查出来有寄生虫,病没治好,在医院活活疼死了——这是后话。
派出所民警尽量息事宁人,但两家的仇恨就此埋下。那之后,高叔叔经常晚上来我家串门,故意先去北屋,不打招呼就推门把头探进屋里,用他那副尊容把人吓个半死,然后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说自己走错了。
爸妈跟北屋住户算是彻底撕破了脸,双方都开始找“道儿上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我爸妈找的是当时北坦的老大,外号叫“老天”,他是北坦的老街坊,老一辈上跟我姥爷有交情。
双方约好的那天,老天带着人来我家跟对方谈判。北屋的人找的也是附近片区的流氓头儿,跟老天也算是认识。认识归认识,事情还得解决。我爸说当时对方口气不善,老天先给对方敬了颗烟,把炉子盖掀开,用五个手指插进烧得正旺的蜂窝煤孔里,把蜂窝煤整个抓了起来给对方点烟。手指在黑红的炭火里烧得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老天面不改色地点完烟,把蜂窝煤又放了回去。对方没说话,抽完烟直接起身撤了。
1986年,西屋和北屋的住家先后搬了出去。我后来问我爸这事儿给了多少钱,我爸说老天就拿了两瓶酒几包烟,其它说啥也不要。
9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有次看到我妈在街上跟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打招呼,后来我妈说那人就是老天。他当时在北坦的街上支了口锅炸油条卖早点,从乡下雇了几个人替他看着。后来大家都说油条里面掺了洗衣粉,生意渐渐就黄了。
3
时代变迁把老天那一代重义气的好汉推出门外,同时又打开窗户迎来新的血色黎明。北坦的居民多为工厂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国企改制,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导致很多家庭生活艰辛。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催收账款、色情行业等灰色产业陆续涌现,北坦崛起了不少黑道人物,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当年济南的黑老大徐宗涛。
徐宗涛家住北坦顺河街的一个大杂院里,距我家只有百十米。他家屋门口有棵石榴树,寓意多子多福。徐宗涛言语不多,但打架下手特别狠,北坦的街坊邻居都叫他“小涛”,我们小孩儿则尊称他“涛哥”。
徐最早在天桥火车站附近摆摊卖家电,1990年以后开始在城南的蔬菜和海鲜批发市场收“保护费”,后来涉足餐饮、娱乐、建筑行业,生意越做越大,手下笼络了不少兄弟,都是狠角色,各自占据一方地盘,形成一统江湖的局面。
徐的“兄弟”中有个人叫杨斌,平时行事低调,有高人给他算命,说他是天杀星下凡煞气重,还说他命硬,只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才是他的葬身之处。或许出于要“上位”的野心,1994年初杨斌悄悄到北坦上门枪杀了徐的父母,徐当晚没在家逃过一劫。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是谁下的手,济南江湖上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徐宗涛到处追杀自己的仇家,甚至把天桥“老大”左亮的四肢都砍断了,也没找到。直到1995年夏天,杨斌在火车站附近的天桥上停车乘凉,巡警偶然间盘查时发现车上有枪支,要对他执行逮捕,杨斌拒捕逃窜,被警察当场开枪击毙。传说他死的时候尸体挂在一棵树上,应验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卦象。
这个案子曾经被拍成电视剧,叫做《济南七·九大案侦破纪实》。片中所有警察都是由本人扮演,高度还原了事件经过。其中时任天桥刑警大队大队长的张龙义后来被提拔为天桥分局副局长,也因为破案与徐宗涛结缘,成了其“保护伞”之一。
1999年,做了十几年济南黑道大哥的徐宗涛被立案通缉,同年底被捕落网,2002年4月4日执行枪决。他被捕之前已经资产过亿,在那个年代也称得上济南数一数二的富豪了。他涉及多起命案,倒台后引发了官场振动牵连无数,其所犯案情的文件用坏了两台打印机,卷宗多到一辆卡车都装不下。
我上初一的时候,在学校里提起我家住北坦,跟“涛哥”是街坊,别人顿时就肃然起敬。对一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来说,被同龄人尊敬和认可的感觉实在美妙。那时我荷尔蒙分泌旺盛,又在学校体育队,于是在飘飘然中也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江湖生涯”。
初中里的“江湖”,无非是一群无知少年学着社会人抽烟喝酒,拉帮结派,在学校里称王称霸,惹是生非。然后大家稀里糊涂拜把子排名次,我当时排行老三。那时候我们经常出没游戏厅台球室“砸钱”——就是寻找合适的落单目标下手,让对方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否则就一顿胖揍。砸来的钱大家平均分,或者找地方去吃吃喝喝。
我的“江湖生涯”止于初二的一次砸钱。那次,有个辍学的朋友叫上我去大明湖砸钱,我还带了把自己磨制加工的匕首。我们找到一个外地来旅游的学生,看我们两个气势汹汹的样子,对方很快掏出了几十块钱。拿钱以后我想赶紧走人,但我那个朋友却看上了人家的相机,可对方死活不同意交出来。
我朋友大概认定对方不敢反抗,就顺手把我带的匕首拿出来,说拿相机玩两天,用匕首做抵押,留个联系方式回头给对方还回去。那个学生被逼急了,接过匕首反手就捅了我朋友两刀,我当时赤手空拳,傻站在一边,眼看着他跑掉了。
事情结局不难想象——我们很快被派出所的人抓获,我朋友是腿上挨刀,医院缝了几针没有大碍。派出所的人看我们年龄小,也没有其他案底,把我教育一顿后通知了家里来领人。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我妈在派出所悲伤的神情让我不知所措,满怀内疚,熄灭了我混社会的冲动和热情。
回家以后,我决定做回一个普通的学生,老老实实补习以前落下的功课。学校里的“兄弟”们觉察到我的变化,也渐行渐远。初中毕业之后,我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回想起那次犯事儿的经过,我总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我也曾幻想过穿越回到那一刻,如果当时我坚持拿钱就走,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我还会是学校里的狠角色,或许结局是既做江湖大哥,又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毕竟当年跟那些兄弟们在一起还是很开心。
后来在同学聚会上听到的消息,彻底粉碎了我这个幻想:据说我当年的“老大”在2006年“扫黑”期间想退出江湖,为了养家糊口开起了出租,有两个东北的朋友来济南找他玩儿,火车站接站后顺道接活儿拉了个女乘客,结果那两个东北人见色起意,等车行至偏僻的地方就把人奸杀了,案发被捕后,老大在法庭上说他曾极力劝阻,但被两人用刀逼着不得不参与,但还是被判了死刑;另一个“兄弟”则跟房地产公司联手干起了暴力拆迁的勾当,因为威胁恐吓伤人等恶性事件,被当替罪羊吃了牢饭。
在我的记忆里,这两个人并非鲁莽之人,相反,他们都懂得审时度势,也熟悉社会丛林法则。从关于他们案情的只言片语里,我再次嗅到了“身不由己”的味道,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是个被天谴的行当,即便深谙世事,依然沦落其中,等待厄运降临。
4
初二决心继续求学之后,我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起来,也更加关注起我家的生活环境。我家没有卫生间,所有人拉屎撒尿都要去街上唯一的公共厕所。厕所靠街那边是黄土墙,墙根有个下水道一样的井盖连到粪池。粪池上面有两排各四个蹲坑,中间用墙隔开分成男厕女厕。蹲坑上面有遮雨棚,其余地方露天。
男厕里有小便池,地上尿液横流,冬天一结冰,让走在上面的人提心吊胆。夏天粪池里密密麻麻蠕动的蛆自不必说,连墙壁的砖缝里都能零零星星爬出蛆来。厕所一墙之隔就是住家,户主姓张,留着络腮胡子,夏日里经常在大门口冷着脸,用水一遍遍冲洗自家墙壁和地面。
夏天蹲坑绝不能穿漏脚趾的鞋,否则感觉到脚趾头缝里的蠕动会让人恶心半天。苍蝇幼虫对鸟类来说却是免费的盛宴,麻雀、鸽子、喜鹊还有些叫不出名的鸟,经常从天而降大快朵颐。夏日里,有时听到空灵的鸽哨从空中掠过,有可能就是圣洁的和平鸽又到这人世间最腌臜的场所去汲取营养升华自己了。
济南三面是山,北临黄河,还是条地上河。大明湖及其周边的泉群,地势最低,是济南的洼地。北坦靠着顺河街,旁边有条宽十几米、深五米的臭水渠,由南向北从高到低承载着市区的工业废水。城市的排水能力是有限度的,降水量超过极限,水渠的水就会溢出来。
我经历过水淹,那次北光明街上的水有半米多深,黄褐色的水里混杂着粪便菜叶塑料袋和各种垃圾,还不时漂过底面朝天的鞋子——这时就不得不佩服我爸妈的先见之明,我家的院子比街道高出不少,水不会倒灌进来。
不少街坊自家院子低,或者几家人混居在一个院里,谁都不愿出钱把院子地面垫高,这时候就只能干瞪眼了。雨过天晴,街两边的晾衣绳上会多出一排排的衣服和带着黄色污渍的被子,墙根儿和窗台儿上则是洗干净的鞋子。
影视作品里常说,以前的四合院或者筒子楼里邻里关系团结和睦,一家孩子吃百家饭长大。那情形,至少在北光明街上没发生过。我家院子当年的事儿自不必说,街上几户大杂院里人多是非多,简直不要太热闹。
以街西头的“高大门儿”来举例,那原本是一处大宅子,门口还保留着以前的门楼,墀头上的缠枝葫芦石雕保存完好。那处宅子的主人早就埋没在历史的糊涂账里不知去向,由于门楼比其他房子都高出一截,街坊们就称呼那个院儿“高大门儿”。
在我印象里,“高大门儿”里的住户,主要是各家的女人们,几乎每周一吵,每月一架。吵的时候,北光明街从头到尾都能听到高亢的女音;打起来,则在街上推搡哭骂,围观人数众多,常常造成交通拥堵。“高大门儿”里的矛盾复杂,我人都认不全,事情缘由实在拎不清,只记得人多势众的那家女儿众多,小名分别是大罐子、大瓶子、大盆子之类的器皿。每次老妈一干架,罐、瓶、盆响作一片,一群娘们儿撒欢儿耍泼,地动山摇。
除了环境的不同,我也深刻体会到了不同地方的人对于获取信息的需求完全不同。之前住在机关大院的时候,门口的传达室也是报纸收发室,每天各家订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孩子们是取报纸的主力军。北光明街上几乎没人订报,买报纸还要去集上的报摊。
另外,机关大院有食堂提供一日三餐,有锅炉房专门烧开水,还有暖气、电话、闭路电视等特权设施,这一切我曾经心安理得地享用。相比之下,北光明街上无人问津的公共设施,还有暴戾而冷漠的人际关系,都折射出了底层生活的残酷。
这种得失对比之间,让我意识到了特权和阶层的存在,也让我打定主意,日后一定要走出北光明街,走出北坦,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追寻一个光明的前途。
5
前面说过,北光明街上的四合院是我姥爷当年购置的。他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铁路部门工作,我姥姥是他中年丧妻以后娶的,比他小很多。姥爷1951年去世,房子后被政府给没收了,姥姥带着还不懂事的妈妈被赶回老家。山东农村重男轻女欺负人的现象非常严重,姥姥回去没几天就备受欺侮,无奈嫁了人,过了没几年就郁郁而终。我妈孤身一人回到济南,投靠了她的舅舅。
姥爷除了我妈还有三个子女,二舅闯关东去了东北中年早逝,大姨嫁去了南京,大舅则在解放前夕随军去了台湾,走那年才十六岁。大舅是跟街上一位姓毕的学长一起从的军,毕学长比他年长三四岁,两人乘火车随军一路南下,到了厦门要上船的时候,毕学长想起了家里的老母和刚结婚的娇妻,犹豫纠结中就没赶上船,留在了大陆。
返回济南之后,毕学长在学校教书,过了几年太平日子。随着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他当国民党逃兵的经历被扒了出来,从此逢批斗必被揪,而施虐者不乏邻居街坊。文革期间他眼睛差点儿被打瞎,关在牛棚差点儿丧命。他的妻子也被牵连受尽凌辱,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但他们顽强活了下来,等到了平反的那天。等我记事儿时,就经常看到毕伯母挽着戴墨镜的毕伯伯从街上走过,悠闲而从容。
大舅撤离到金门驻守,退伍之后在大学读书,勤工俭学时认识了大舅妈。大舅妈是台湾本省人,家境殷实,两人后来在女方家族的资助下共同赴美求学,毕业留在美国大学教书。大舅的儿子,我的表哥,有次突然问他为什么要在国外而不是回自己的国家生活,大舅思考了很久,决定举家回台,后入职成功大学,担任教授直至退休。
文革结束,两岸恢复往来,大舅从台湾来信询问亲人的下落,才知道有我妈妈这么个小妹。我妈1985年应邀去香港跟他第一次见面,1991年大舅在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后首次返乡探亲,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宅。
由于大舅属于知名学者,闻讯而来的老街坊和街道办、侨办人员络绎不绝。我家的小院似乎从未这么热闹过。毕伯伯夫妇当天也联袂而至。两位好友见面很是感慨,相互诉说各自经历之后,大舅提起当年参加毕伯伯的婚礼,新娘子名门闺秀、如花似玉,让大家惊为天人,只羡鸳鸯不羡仙。当时两个人弃笔从戎,本想做一番事业来抚慰满腔热血,结果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这些年来,他惦念着老友,也由衷敬佩老友当年毅然折返的勇气,“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老婆太漂亮了,换了我,也舍不得一个人就这么离开”。
毕伯母羞涩地说:“都半老徐娘了,不复当年风采。”毕伯伯哈哈大笑,紧握着妻子的手,环视围坐的街坊邻居,豪迈地说:“人生无常,唯有坦然面对,我从未后悔当年的选择。”两人起身告辞,携手悠然而去。
多年以后我在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时,情不自禁地想起毕伯伯和毕伯母。一样普通的城市和街道,一样有着平庸之恶的人们,都见证了闪耀着人性光明的灵魂和爱情。
大舅探亲给我很多触动,在那个以有海外亲戚为荣的年代里,我家成了北坦地区为数不多的侨属,逢年过节经常有街道办领导上门拜访。抱着对未来的向往以及对前途的思量,那之后的时光单调而平凡,学习占据了我所有的生活。高中毕业,我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离开北光明街,离开那条肮脏的、充斥着不公不义与黑暗的街道。大二时,我被公派去欧洲留学,走上了跟初中兄弟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济南和家,一道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这期间我曾偶尔回家短暂停留,作为看客目睹了随着顺河街高架桥开通,临街洗头房曾如雨后春笋,入夜后红灯交相辉映的繁荣“娼”盛。也见证了随着人口涌入,破旧的社区更加拥挤不堪。
很长一段时间里,意气风发的我也庆幸自己永远远离它,远离与之相关的一切了。
2010年,北坦陆续完成了棚户区拆迁,我爸妈在大明湖附近住了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就选择在附近买了商品房。新家小区在一条新修的水渠边上,源头是大明湖和趵突泉泉群,渠深十几米,水道宽阔。
几年后,北光明街消失在了时代的洪流中,原址现被购物中心所取代。济南在重点开发东部的高新区,那边有着广袤的土地,以前的老城区逐渐沉寂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跟我在南方待过几年,可故土难离,后又回到济南。只是,母亲抱怨居民楼隔音差,楼上住户吵得她睡不好觉。她常常怀念曾经的老宅,说那里“接地气、风水好”,怀念曾经的街坊走动频繁,不像现如今邻居见面不相识,来来往往都是陌生人。那条街上的腌臜往事仿佛都被她一一抹去,镀上一层温馨、甜蜜的荣光。
随着老街消失,我儿时的记忆也渐渐淡去。人到中年,历经世事,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我知道那些黑暗与不公不义不仅只存在于曾经的北光明街上,也不止只存在于那个时期。而我少年时所想要追求的“光明”,或许不是走出北光明街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的,那只是我的起点。
作者:百纳
编辑:唐糖
题图:《童年往事》剧照
点击此处阅读网易“人间”全部文章
关于“人间”(the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关注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只为真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