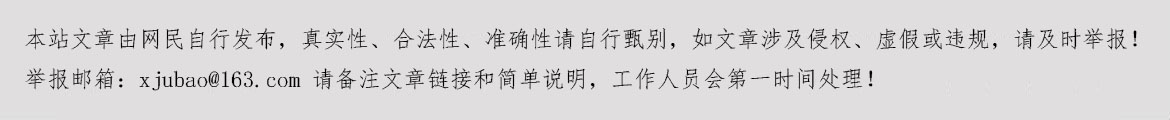一
春蝉刚睁开眼就看见已经殡天的皇帝坐在自己的棺椁上悠哉地往嘴里送一块供果。身边胡乱丢着入殓时带在头上的顶冠,随意撸上去的袖子露出半截手臂在这地宫明亮又阴森的长明灯中,泛着悠悠的冷白。
春蝉心说皇帝死了果然和寻常百姓不同,在地府中想如何就如何。自己这次跟着殉葬是来对了,做鬼也能做个颇有地位的鬼,待日后找到奶奶就能相互照应着在幽冥鬼城好好生活下去。
奶奶是春蝉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和吃供果的皇帝同一天过世。
也因为奶奶的过世,春蝉成了偌大的皇宫中唯一一个自愿殉葬的人。
春蝉还记得当她在满室压抑的哭声中朗声说出:“我自愿去。”这句话时,掌事姑姑眼中的震惊和惋惜。
“你当真愿意去?”掌事姑姑一改往日的沉稳,几步跨到春蝉面前,一把扯住她问。
从接到圣旨的那一刻,掌事姑姑的心就像放在油上煎,传旨的公公与她是同乡,私下里悄声对她说:“你就知足吧,只让你们御膳房的宫女陪葬一人,王公公那边连他自己都得赔进去。”
可这些宫女也是她看着长了四五年,青春正好的女孩子啊,无论谁去都是从她手里推出去送死。
想来想去只好昧着良心把手下的宫女们叫到一处说:“当今圣上殡天,要从咱们中间选一个人殉葬,能伺候先皇是有大功德的,无论自己还是家人生前死后都能得到庇佑。”
说到一半的时候就听到此起彼伏的哭声响起,压抑着的哭声让掌事姑姑的喉咙泛出阵阵酸涩。
她想好了最终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去,生死有命吧,这是她能想到最公平的办法。
可万万没想到春蝉会冒出来,这孩子平时话少,手脚麻利,干活从不投机取巧,一双黑漆漆的眸子衬在圆圆的鹅蛋脸上总是让人心生沉静。
抓住春蝉的手臂微微用力,她在暗示此刻后悔还来得及。
可春蝉的目光清澈可见,脆生生的说:“姑姑,我愿意。”
顿时,其他宫女呼啦啦围了过来,春蝉成了英雄,掌事姑姑被挤在人圈外面最终无奈的甩了甩手里的帕子。
就这样,春蝉当天就被送到祈福宫和其他殉葬的宫人沐浴斋戒准备七天后和先皇一起葬入皇陵。
祈福宫中不时有人逃跑,水米未尽的春蝉亲眼看着逃跑的宫人被抓回来,当着其他人的面活活勒死,可那临死前青紫的脸和暴突出来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反而更加激发了众人心中的恐惧。
随着逃跑的人不断增加,负责此次殉葬的钦天监不得不请了摄政王的旨意,在先皇葬礼的前两天调了大批的御林军,将所剩不多殉葬宫人分批处死。
已经五天没吃没喝的春蝉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着眼前四散逃窜疯狂挣扎的宫人,她惊讶为什么大家还有这样的力气,直到一双黑色官靴停在她的面前。
春蝉抬起头看到一个身穿护甲的髯须汉子手执三尺白绫要绕上她的脖颈,她连忙露出讨好的笑用尽力气大声说:“大人,我愿意饿死,您看我没跑,求您别勒死我,那样死法我地府里的奶奶见了害怕。”话到末了已带了哭音。
三尺白绫还是落了下来,春蝉的呼吸一下憋在了胸口。
二
斜上方的皇帝还在大吃特吃,雪花梨入口嘎嘣脆的咀嚼伴随着甜美汁水爆裂的声音刺激着春蝉的耳朵。她不禁暗骂:“昏君,死也不让人做个饱鬼。”
许是为了配合春蝉,她的肚皮随之发出了极响亮的声音:“咕噜咕噜咕噜噜。”
坐在棺材上的年轻皇帝顿时像被施了定身法,接着眼睛缓慢的转向春蝉的方向,正对上春蝉望过来黑亮亮的大眼睛。
四目相对,春蝉想起在宫里听到这位皇帝的残暴事迹,慌得想挣扎起来却毫无力气。
大着胆子抬眼再看,就见年轻的先皇向前探着身体直勾勾的盯住她,声音微颤着问了句:“你也是活的?”
春蝉脑子里放映出最后那髯须大汉恻隐的眼神和卷上脖颈没有下死力的白绫,终于反应过来自己没死。
心中不免一阵失望,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脚步声缓缓走近,春蝉被扶起来靠在年轻先皇温暖的怀里,一股淡淡的酒香飘进她的鼻子,接着她的唇碰到冰凉的杯沿,清润的果酒缓缓注入她的嘴里。
这昏君要干嘛,春蝉前一秒还在为自己活着而感到痛心,后一秒就发现这传说中的昏君竟意图救她。心中顿时憋了一口气,活着的时候不让人吃饱,现在离饿死就差一步了又要把人救回来,索性横了一颗心任由果酒灌了满嘴就是不往下吞咽。
元霏看着灌进去的酒顺着春蝉的嘴角又流了出来,以为人又死了过去。赶忙伸手去探春蝉的心跳,却在手刚刚触到春蝉隆起的胸前就见小宫女颤抖一下睁开了眼睛。
“没死就好,”元霏把剩下的酒灌进春蝉嘴里,却发现还是之前的样子,才反应过来这小宫女是存心不喝。
元霏不解的放下手中的杯子,扳过春蝉的脸问:“你不想活着?”
见春蝉双目紧闭也不说话,元霏突然轻笑:“朕偏让你活着。”
说完就又端了手中的果酒,却是另一只手捏住了春蝉的鼻子,就这么半呛半喂的把大半杯果酒给春蝉喂了进去。
让春蝉进食仿佛成了元霏的乐趣,渐渐的春蝉开始有了力气,会在元霏扶她起来的时候挣扎两下,说出的话有气无力的总是那么两句:“我不吃,陛下别再喂了!”
元霏的耐心在春蝉反反复复的绝食和絮叨中消磨殆尽,看着手中喂了十多次都没能成功的核桃酥和自己一身的点心渣忽然冷笑:“你就这么想给朕殉葬?”
看春蝉垂眸不语,元霏突然抬手扯了她的头发转向后方:“你想像他们一样,是吗?”
春蝉抬眼望去,这才发现在自己身后是一排排盘膝而坐,面色青紫早已死去多日的宫人,顿时吓得惊叫一声往后缩着撞进了元霏的怀里。
“怎么,怕了?”元霏阴测测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你不是一心求死吗?饿死太慢了,朕可以更快的成全你。”说着,一双冰凉的手就掐上了春蝉的脖颈。
一瞬间春蝉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从元霏的怀里挣脱,哆哆嗦嗦的趴伏在地上:“陛下,陛下饶命。”
元霏看着她害怕的样子和从前的宫人没有两样,眼中凉薄之色更甚,嗤笑一声:“现在想让我饶命?晚了。”
春蝉不敢抬头,心知掐死一个宫女这种事情对于元霏而言不在话下。
被勒死的宫人恐怖的面容犹在眼前,她哭着连连磕头:“求陛下别掐死我,我还要去阴曹地府见我的奶奶。”
元霏闻言思考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小宫女是觉得被掐死后死状恐怖,影响了去见死去亲人的形象。目光扫过面前那一排排生前被活活勒死扔进来殉葬的宫人,忽然一股怒火油然而生。
拉起春蝉狠狠掐住她的脖颈,阴狠地说道:“朕凭什么成全你。”
春蝉的脸由苍白变为涨红,眼中的惊慌哀求变为绝望,这绝望的眼神居然和元霏每每夜深人静时看向镜中自己的目光那般相似,他忽地放开了手。
重获呼吸的春蝉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本就饿的半死不活的身体顿时承受不住,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三
这才是真正的地府吧,和奶奶曾经说过的一模一样,忘川河,奈何桥,不同的是桥头一个摇曳生姿的女子居然长了张和皇陵中元霏一模一样的脸,手捧一碗孟婆汤笑吟吟地递给春蝉:“来,小姑娘,喝了这碗孟婆汤。”
春蝉连忙摇手:“姐姐,我奶奶就在前面,我追上她一起来喝!”
女子一听就变了脸色:“不行!不喝孟婆汤就踏不进这酆都城!”
春蝉急的苦苦哀求:“姐姐,喝了这孟婆汤我就记不得奶奶了,求求您让我进去,找到奶奶我一定出来喝,喝多少都行。”
谁知那女子怎么都不依,拉扯间面目逐渐狰狞,捏住春蝉的下颚恶狠狠的就把一碗汤灌了下去:“到了这里就得听我的,我让你喝就得喝!”
春蝉被呛得连连咳嗽,大睁着眼睛躲避,却看见眼前人不知什么时候换做了束发的元霏,正捏着她的下巴给她灌一碗米酒。
原来只是一场梦,春蝉突然间悲从心起,她的命从不由自己,村里人说她是灾星她就得是灾星,婶婶说让她进宫她就得就进宫,现在就连死都不能由自己做主。
想到这儿顿时连挣扎的心都没了,就那么呆呆的任由一碗酒淋淋漓漓浇湿了衣襟。
元霏发觉春蝉突然变得安静下来,豆大的泪珠从少女漆黑的眼中大颗大颗的滚落,落在他手上竟是灼烫。
烦躁的一把丢开手里的碗用袖子胡乱擦了把春蝉的脸:“行了,哭什么哭,朕和你玩笑呢。”
见春蝉还是呆呆落泪,再看看面前满地的死人,元霏的心头也涌上一阵悲凉。
从小到到大没有人教过他善恶对错,只教会他肆意妄为。自从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笑话和傀儡之后就更加变本加厉的仇视身边的一切,只觉得活着一天就要折腾一天却一天比一天了无生趣。
直到那天和王美人歌舞升平畅饮了三天三夜,朦胧中他感觉自己呼吸加快浑身无力,四下是惊慌的哭喊声。当听见太医那老迈的声音颤抖着说:“秉告摄政王,老臣无能,皇上怕是回天无力了。”
那一瞬间元霏丝毫不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报复成功般的快感。
可他想不到自己居然没死,在硕大的棺椁中醒来之后元霏从诧异到惊恐再到最终的开怀大笑,他终于不用活在他人笑话的目光中,不用再每天任人摆布,哪怕是身处这偌大阴森的皇陵他也愿意。
元霏的手拭去春蝉脸上的泪水,梦呓般地问:“皇陵中食物有限,酒水有限,终究是要死的,你就当陪朕多活几天还不行吗?”
春蝉眼睛眨了几回,转回到元霏脸上,少年皇帝面若美玉,那一双向来凉薄的眼睛溢出少见的脆弱,此刻元霏的语气和自己进宫的那个夜里奶奶边给她拭泪边说:“进宫总比我哪天死了他们把你卖到烟柳巷去的好,你就当为了让奶奶安心行不行?”如此的相似。
叹了口气,春蝉捡起地上几天前散落的糕点,慢慢塞进嘴里一口一口的嚼了起来。
元霏看她终于肯进食心下松了口气,寻觅了各色吃食摆在她面前。
连续两天,就像捡了一只小猫般,元霏细心的把春蝉的命救了回来。
四
“你说你叫春蚕?真是有趣儿,起个虫的名字。”元霏偏头对春蝉说。
春蝉刚咬了一个爆汁的蜜桃,顿时一口汁水喷出来溅了元霏一身,她赶忙从腰间抽了帕子边擦边说:“不是春蚕,是春蝉,蝉。”
元霏嫌弃的拂开她的手帕:“还不如蚕呢,起码人家活的久些。”
春蝉却毫不在意地继续帮他擦净了衣服上的汁水:“活长活久不就那么回事儿,不能和想念的人在一处,活多久都没意思。”
元霏从来没有想念的人,他体会不出春蝉的感觉,但突然之间他很想知道让春蝉想念并甘心赴死的奶奶是什么样子。
心里想着,嘴上就问了出来。春蝉没想到元霏会问她这个,但还是脱口而出:“我奶奶是这世上一等一的好人。”
为了知道这世上一等一的好人到底是什么样,元霏在阴森的皇陵中摊开了笔墨丹青,按春蝉讲的画了下来。
春蝉在一旁讲的详细看的认真,不时地指着一处对元霏说:“这里脸再圆点儿,嗳,过于圆了。”少女特有的馨香传进元霏的鼻子,笔尖一顿,一滴浓墨落于纸上慢慢洇开。
“哎呀,好不容易有一张3分像的,这……”春蝉一脸心疼地看着被墨污了的画,元霏大笑着一把扯过来团了扔向角落,“吃饭吃饭,吃饱了朕再画好的给你。”
这副好的却始终画不出来,后来元霏索性执了春蝉的手让她握了笔细细勾画,随着纸上线条越走越多,两人的手上都逐渐出了汗,春蝉不安的挣了挣手不想被元霏握得更紧,皇帝的气息就在耳畔吹的她脖颈酥痒:“别动,再动朕就又画错了。”
有时元霏也觉得奇怪,从自己初经人事后环肥燕瘦各种风情的美人见了无数,如今怎么会对这寻常的小宫女把持不住。
便狠了心不去理她,可春蝉却好似全不在意,仿佛元霏理不理她都是理所当然,更不会像以前宫中的美人那般费尽心思讨他欢心。
想到这里,元霏开始在死去的宫人中找曾经自己宠爱的美人,却发现早已忘记了那些花朵般的脸庞长的什么样子。
反而是春蝉,不美艳不出众但就是那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衬在白净的鹅蛋脸上,安抚了他从小到大积存的怨念和戾气。
小宫女轻哼着家乡的民谣手脚麻利地整理着棺椁中的被褥,因大厅中气氛实在过于阴森,元霏早就把自己的棺椁分了一半给春蝉同住。反正这硕大的棺椁即便再挤两个春蝉进来仍显得宽敞。
夜半时分元霏每每醒来看见春蝉面朝棺壁的小小背影总会不自觉勾起唇角,轻轻的伸手捋过她一绺黑压压的头发绕在指尖。
可春蝉却越来越不快乐,她吃的越来越少,甚者有的时候会一两顿不吃,可又在元霏发脾气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着食物。
终有一天春蝉仿佛下了大决心,在元霏又拉她画画之时郑重地跪在元霏面前磕下头去:“陛下,春蝉要去了,陛下一定好自珍重。”
元霏看着跪伏在地上的春蝉,心慌的仿佛手下的笔就要戳进自己的心窝。相处久了他愈发了解春蝉的倔强,此刻她重新提出要死便是又抱了必死的决心。
沉吟良久后元霏开口说:“春蝉,朕给你画一幅画吧。让你的画像代替你来陪我。”
五
画像之前元霏让春蝉换上了牡丹薄水烟的裙衫,又帮她把头发梳起鸾凤髻,为她薄涂脂粉后,手指沾取轻轻一点胭脂落于少女粉色的唇间。
硕大的棺椁中春蝉侧卧于锦被之上,因元霏说外面那一屋子的死人会败了他绘画的兴致。
水墨丹青一笔笔勾勒春蝉的眉眼,元霏听到面前的少女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那是他在为她轻点绛唇时在小指盖中混进去的一丝迷情粉末。
多亏他在位时是个昏君,这些淫欲之药从不离身,也亏得办事的人敬业,竟给他原原本本挂在身上带了过来。
迷情药的分量并不重,春蝉也只是呼吸急促香汗淋淋,但神志却是清醒。元霏伸手抚上春蝉的肩头,他紧张的摒住呼吸,做了十八年的皇帝,居然需要用迷药这样的手段才能把心爱的少女留在身边。
元霏的手沿着少女的肩膀滑至腰间,春蝉的身躯在元霏炙热的手掌下轻轻颤抖,元霏一只手撑在春蝉身侧,少年郎身上的龙诞香随着他的体温升高变得越发浓烈。
春蝉失神中看着皇帝俊美的脸颊一寸寸靠过来,元霏生平第一次求人,他轻啄春蝉的耳垂呢喃道:“春蝉,多陪我几天,我们一起死,死后我陪你去找奶奶。”
第二天,从疲惫中醒来的春蝉看着身旁睡得宛如婴儿般的元霏,在心中轻轻叹息:“奶奶,求您再等等我。”
爱情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哪怕是眼前的墓室。
皇陵中的气味开始变的越来越不好,宫人们的尸体虽然涂抹了水银,但依然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陪葬的食物变得日益坚硬,需要拿果酒细细泡了一同饮下,果酒的坛子也日益渐空。
春蝉和元霏逐渐变得虚弱,经常相拥着躺在棺椁里,元霏爱听春蝉一遍遍给他唱自己家乡的民谣,听春蝉讲她家乡油绿的水田,小时候骑着水牛被摔下来后脑勺留了很长一道疤。
元霏想如果早点遇见春蝉他一定不让这姑娘受这么大罪,可如今他能做的,只是留住春蝉的性命,哪怕只有几天也好。
可春蝉还是明显的虚弱下去,变质的食物和酒水让她和元霏经常呕吐不止,但她依然面带微笑时刻握紧元霏的手。元霏知道该是带春蝉去找奶奶的时候了。
按照春蝉的想法,死亡依然是以绝食的方式开始。
硕大的棺椁中元霏和春蝉相拥而卧,元霏仔细倾听着春蝉微弱的呼吸,他怕春蝉先他一步离去,黄泉路上再寻不见。
忽然他听到地面仿佛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原以为是临死前的幻觉,却不想伴随着脚步声是皇陵沉重的大门被吱呀呀推开,接着就听到一众人抽气的声音。
“娘的个乖乖,这元霏的陵墓当真是富可敌国呀!”这声音在元霏听来竟有些熟悉。
“娘的,让老子来给他个黄毛小儿守陵,老子今天就把他的皇陵洗劫一空,让元姜这老杂毛的儿子死后也不得安生。”接下来的这句话仿佛一记重锤砸的元霏痛彻心扉。
已经多日不曾想起,他是摄政王元姜和前朝宠妃程灵璧苟合后生下的野种,但毫不影响这是满朝皆知的秘密。
摄政王元姜不愿背负篡位的罪名,遂把小小的他扶上王位,纵他护他却从不教他,只有元霏是个废物,他才能坐稳摄政王的宝座。
元霏庆幸此刻的春蝉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从前地位地下的她还没有听说过自己这不堪的身世。
“这是什么规矩,棺材盖只盖了一半。”一道黑影挡住了元霏头顶的光,“呦呵,这还搂了个小娘们儿。”
一直漠然不动的元霏陡然睁开眼睛坐起身来把春蝉护在身后,抬头之际认出来人竟是自己的舅舅,当朝大将军程堰。
饶是程堰手握重兵杀人如麻,也扛不住亲眼看到已经死了月余的元霏从棺材里直挺挺坐起来的惊悚,拔出腰间的长刀就劈了过去。
电光火石间元霏猛地向后一躲但还是被劈进胸膛一寸有余,意识消散之前他不忘摸索着抓住春蝉的手。
六
元霏朦胧中感觉握住的那只手几次三番要抽出去都被他硬拽了回来。直到耳边传来柔媚的声音:“陛下,奴婢服侍您换药呀。”
睁开眼,视线由模糊渐渐变为清晰,面前是一张千篇一律妩媚的笑脸。元霏看清自己握住的手是面前这女人的,连忙厌恶的一把丢开。
他刚醒来时已经有机灵的婢女脚步匆匆前去禀报,元霏控住不住心中的惊慌沉声质问:“春蝉呢?”
面前的婢女迅速反应过来,忙柔声说道:“是和陛下一起回来的那位宫人吗?大将军安排了在侧院医治呢,想来没有大碍。”
闻言元霏憋在胸腔里不敢呼吸的一口气才吐了出来,还不等吸气就听门外沉重的脚步声快速由远及近,伴着程堰粗大的嗓门:“元霏我的好外甥,你可吓死舅舅了。”
说话间人已撞了进来一把扶住元霏的双肩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又揭开元霏胸前的纱布细细端详后才如释重负般叹气道:“好在你没事,不然我怎么有脸去见你死去的母亲。”
元霏看着眼前的程堰,知道这人此刻的热情事必有妖。
扮演完舅甥情深的程堰见元霏垂目不语,眼中闪过一抹不快。
但很快就似压抑不住的怒道:“你那不是人的叔叔就是乱臣贼子,可怜你堂堂当今圣上,被他压制在后宫之中,最后郁郁而终。”
元霏眼中涌上晦涩不明的笑意:“舅舅错了,我已经不是什么陛下,如果真要论,舅舅应该称我一声‘先皇。’”
“说哪里话,殡天才是先皇,你现在好端端的活着,就是当今陛下。”程堰急切地说道。
接着越发义愤填膺的说:“你可知,前脚刚办完你的丧葬大礼,元姜就顺势准了礼部的折子准备起了他的登基大典。”
见元霏眼中闪过几分意味不明的笑意,程堰的心中不禁狐疑,他印象中的元霏暴戾易怒,可现在看来这少年死了一次之后仿佛心性沉静了许多。
想到这里便话锋一转:“还好陛下福泽深厚,也亏得是老夫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去为陛下守陵,方能及时将陛下从皇陵中救出,元姜此次的篡位必不能得逞。”
元霏的小指扫过眉角,若不是这老匹夫当初迈入皇陵时那一句“洗劫一空,r让自己死后都不得安生”的豪言壮语犹然在耳,他可能就信了程堰此刻的忠肝义胆。
程堰见自己几次三番的挑唆都像重拳打在了棉花上,心知如今的元霏已经不似往日,自己心中所谋亦不可操之过急,打了个哈哈让元霏好生休息就从房中退了出来。
自始至终,元霏都没在程堰面前问起春蝉半个字。
尽管心中担心春蝉几乎到了五内俱焚的地步,但他知道宫廷中的争斗肮脏残忍,程堰接自己回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他的关心只会让春蝉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可元霏低估了程堰,这老匹夫纵横官场数十年,从皇陵中见到奄奄一息的春蝉时便嗅到了这少女对元霏而言非比寻常。
初更时分程堰传来了伺候元霏的婢女,细细询问元霏醒来后的情景,待听得元霏刚一醒来便找寻那名叫春蝉的宫女时,程堰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
一连半月过去,元霏在医官的精心调理下日益强壮,胸前的刀口也渐渐愈合,他常装作不在意的问起春蝉,得到的消息却从一开始的“想必没有大碍”,变作后来的“奴婢不知,已经两天都不曾听到那位宫人的消息了”。
元霏心中越来越慌,终于让婢女传话,他要见程堰。
程堰等的就是元霏主动上门,此刻的他就像一个洒下鱼饵静等元霏上钩的渔夫。
在密室中程堰向元霏历数摄政王元姜多年来专权跋扈祸国殃民的条条罪状之后,终于把话题转到了元霏身上。
“陛下正值盛年,却被元姜逼迫至死,如今天佑陛下圣体康健归来,老臣怎能容忍真龙天子流落民间,奸佞之臣谋权篡位之事!”
看着面前慷慨激昂吐沫横飞的程堰,元霏完全没有配合他演戏的欲望。
他单刀直入打断了程堰的话:“舅舅无外乎是想朕继续回去当皇帝,朕答应就是了。”
不等程堰的一大堆赞美之词出口,元霏已带了焦灼问道:“还请舅舅告知当日和我在一处的宫女现下如何。”
春蝉自然安好,有这样一条挟制元霏的大鱼,程堰怎会不好生救治。
程堰看向元霏的目光中透出阴谋得逞的得意:“陛下,春蝉姑娘很好,老臣会交代下去从今日起陛下随时可去探望,还要恭喜陛下春蝉姑娘已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七
再见春蝉,元霏觉得恍如隔世,少女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已飞扑了过来,慌得他赶忙拦腰将她抱起小心翼翼地放于床上。
春蝉胖了一些,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元霏觉得春蝉的腰已微微见粗,娇憨的脸庞枕在元霏腿上,柔和的光线下春蝉脸上的一层薄薄的绒毛让此刻的她像极了一颗饱满的蜜桃。
“马上就要当娘了,以后万事都要当心,不能再这样跑跑跳跳。”元霏轻轻刮着春蝉的鼻子。
春蝉顺势抓住元霏的手指放到嘴边有一下没一下的轻咬着撒娇:“知道啦,陛下——”
一声陛下居然叫出了元霏的眼泪,用力瞪回了眼中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元霏轻轻遮住春蝉的眼睛:“要是男孩就叫元识,若是女孩就叫元初,以纪念你我初相识之意。”
春蝉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拿开遮住她眼睛的手:“我梦见奶奶的时候,奶奶还说一定是个大胖儿子,叫元宝。”
元霏也被春蝉逗得开心起来,捏住她的鼻子:“好,元宝就元宝。”
门外的婢女小声地催促:“陛下,天色已晚,陛下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
元霏淡淡地应了一声,春蝉好奇的翻身坐起:“你今晚不留在这里吗?”
元霏扶她躺下,细心地帮她掖好被角:“朕还有好多事忙,在这里怕扰了你的睡眠,明日一早朕就来看你。”
闻言春蝉虽然十分不舍但还是乖巧点头,在元霏身影即将消失于门口时,突然轻声唤住他:“元霏,奶奶说让我不要再牵挂她,她说让咱俩好好活。”
元霏轻嗯一声,就逃一般的飞出了春蝉住的小院。
从古至今就没有死而复生的皇帝,元霏知道自己只是程堰击垮摄政王的一把利刃。事成之后,必不会留他在世上。当日的密室一谈中,元霏答应了程堰的所有条件,而作为交换,程堰必须放春蝉母子性命。
程堰诧异的看向元霏:“陛下说的哪里话,春蝉的孩子也有四分之一我程家的骨血……”
不待他说完元霏就打断了他的话,目光灼灼如炬:“舅舅要用程家上下老小的性命起誓,终生不得害她们母子性命。”
程堰在与元霏的目光碰撞之下最终妥协一笑:“我程堰以程氏满门性命起誓,不害他们母子性命。”
又过了几日,元霏让春蝉收拾了些细软,带她坐上了回鄉的马车。
一路上春蝉开心的像个孩子,不时撩开帘子探头去看,忽然又想起来什么,拉住元霏的手:“元霏,我们应该买些日常家用的东西,乡下的房子空置了这么久,能用的东西怕是早被婶婶拿了去。”
元霏安抚的拍拍她的手:“不急,回头缺什么咱们再买。”
直到真正到达家中春蝉才明白元霏所说的不急是什么意思,自家那破旧的老屋已被翻修一新,院子扩建了两倍,家具用品焕然一新,从外到内贴满了喜字,院中站着两个老妈子并两个年青丫头,都打扮的极为喜庆,为首的那个快步迎上来挽住春蝉的手:“新娘子终于来了,奴婢在这里祝新郎新娘新婚大喜。”
春蝉泪眼朦胧的望向身侧的元霏,不等泪落下已被他温柔的手指拭去:“这么喜庆的日子,我的新娘子可不许哭。”
夜晚,元霏小心的搂了春蝉在怀里:“春蝉,朕明日就要走了。”
怀中的人一震却没有说话。
元霏安抚地轻拍春蝉的背,说出了酝酿许久的谎言:“朕又没死,自然是要回宫的,只是……朕暂时不能接你回去,你别怪朕。”
闻言春蝉明显身体一松:“我怎么会怪你。元霏,你今日许我的这个婚礼便是我毕生的欢喜。”
“宫里肮脏龌龊的事情太多,朕也不见得事事都能护你周全,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这里好。你放心,朕只要一有时间便来看你,好不好?”元霏小心翼翼的问。
“好,”春蝉答应的很是干脆,“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不见天日的皇宫里出来,才不要再回去。”
又拉了元霏的手仔细勾画他的掌纹:“只是你要记得常来看我,还有元宝。”
元霏用力的将春蝉勒紧在怀里,小心的将右手放在她的肚子上,轻声应好。
八
程堰举事的前一天元霏将20封早已写好的家书整齐的交于程堰手上:“烦请舅舅将这些书信每月一封帮我寄给春蝉。”
程堰眼皮跳动了一下,双手接过,嘴巴开合两下却见元霏已朗声笑着走了出去。
前19封书信足以陪伴春蝉从孕期到产子出月,而第20封书信则是一封绝情书,就让春蝉以为他最终薄情寡义而憎恶他一生吧,也不要这傻子像当初为了她奶奶一样也为了他甘心赴死。
元霏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春蝉的当天,一直将他送到村口的春蝉还没来的及回家,就被程堰派去的杀手从背后一剑刺穿了心窝。
正元十九年,摄政王元姜的继位大典上大将军程堰率兵谋反失败,所随众人皆被当堂射杀。程堰满门老小三日后皆被处斩。
尾声
五日后,从程堰府邸查抄出的20封信笺连同信封中的一块玉佩呈到了元姜的面前。那块通体翠绿的灵犀双环佩还是元霏5岁生日时由自己亲手为他带上的。
元姜的眼线早就探知了程堰的阴谋。那日皇宫中埋伏的弓箭手多如牛毛,文武百官早在他的授意之下假意和程堰串通,只等宫人打扮的元霏被推出来就矢口否认他是皇帝的身份。
元姜没想到最先否认的是元霏自己,少年依然挂着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慵懒笑容:“大将军说什么呢?我不过是大将军从乡下带回来的一个书童,怎么就成了大将军口中的皇帝?”
心知大势已去的程堰抽刀刺入元霏的腹腔,同时如雨的箭矢铺天盖地向程堰那一众人射去。
自认为心硬如铁的元姜终于老泪纵横,手指颤抖着拂过整齐的书信,吩咐贴身太监:“烧了吧。”
同一时刻酆都城中春蝉正被眼前面如冠玉的少年纠缠的心烦:“都说了不认得你,你怎么还日日过来?”
忽然被人拍了拍肩膀,负责送信的鬼差递过厚厚的一沓信笺给她,春蝉疑惑的展开其中的一封,只见头一行写着:“春蝉吾妻,见字如面……”